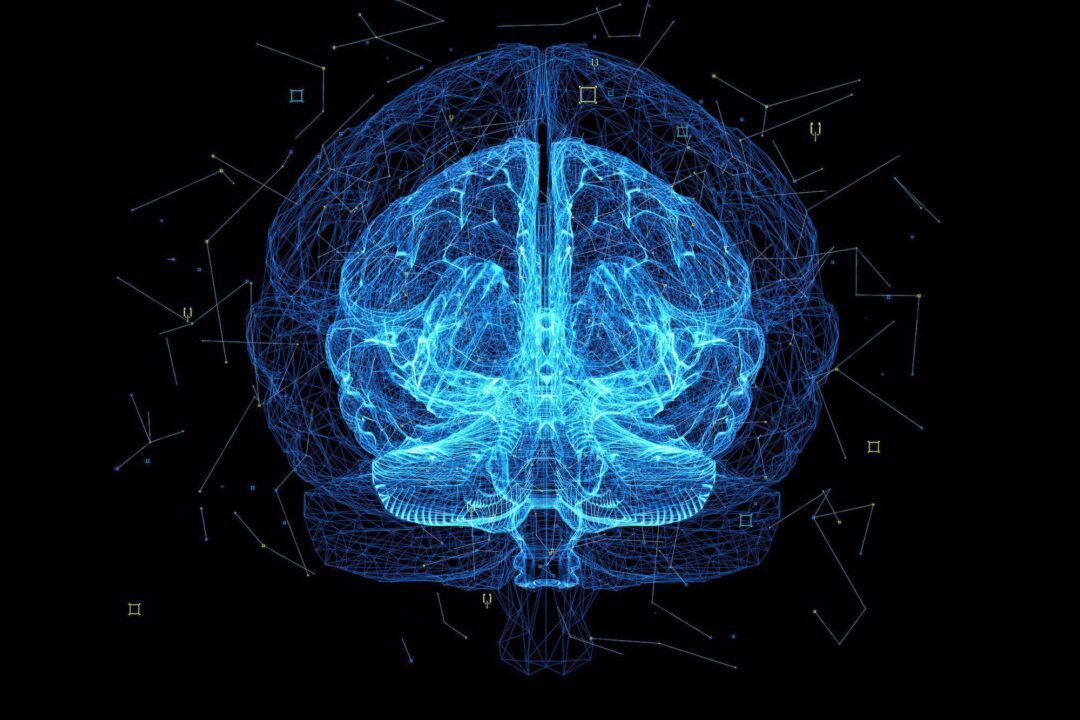我一向想象力非常丰富。孩提时代,我常盯着自己的手,眯着眼睛看向掌纹缝隙深处,观察一个个充满外星生命的小小世界。我会想象整个外星文明如何碌碌终日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它们生活的整个世界只是我掌中的一小块皮肤,而它们的所有活动只是为我的生命系统助益而已。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想象与事实相差并不太大。
我们每个人身体中都包含一首生命的交响曲,尽管这首交响曲要比那时的我能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更加复杂多变。我们人类是一系列精细协调、相互关联的生物系统。这些系统由仅仅二十种基酸的结合体构成。这些氨基酸则由四种核酸串联出的双螺旋引导。这四种核酸经由我们人类之手,创造了我们已有的一切。
卡尔·萨根有句名言:“我们人类是宇宙了解其自身的一种方式”。不过这个说法未免有点自大,“我们”只不过是精密的生命机制的产物而已。生命机制历经极漫长的摸索试错,随机的步伐中每一步前进都增强了我们的适应性,赋予我们必需的特质,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了解自身及我们所生存的宇宙。
关于我们人类的存在,一个有趣的说法这样区分我们人类和所有其他已知物种:人类总是在探询自己是如何诞生的,又为何会诞生。我们当中有些人不满足于所处时代给出的解释,于是针对这些问题继续上下求索,造出工具拓展我们探索未知的能力、增进我们对所有一切的理解。
我们学到的所有东西中有一课至关重要:生命从未停止变化。我们基因构成中数不尽的变异和细微变化推动生命的自我演进,这一过程永不停息。大部分情况下,那些改变毫无影响或影响甚微。偶尔,那些改变会带来优势。
然而,时不时的,那些改变也会带来极其残酷的损害。
从我症状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而从某些小问题最初出现算起,可能已经有二十多年。尽管我很庆幸我机能衰退得还算缓慢,我已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病症那无情前进的脚步。这些日子以来,我很少有哪一刻不感觉到它的影响。它几乎影响到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此刻,我敲下你正在读的这些字的时候,也不例外。
写这篇文章的大部分时候,我要么难以动弹,努力移动自己僵硬迟缓的胳膊和手指,勉力打下想说的内容;要么颤抖不停,努力控制运动障碍导致的右臂和腿的不规律震颤。简直不敢想10年以后情况会多糟。不过,忧心于未来毫无意义,应付当下的每个时刻已经非常不易,更别提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在过往无数代孜孜求索的先辈的集体智慧基础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答案更近,即将探明让我们最为不解的谜题,即人体深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尽管在已知和我们需要了解的未知之间依然存在着令人生畏的鸿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现在取得的进展将会揭示我们系统出错原因的关键洞见,并为我们提供正确干预所需的工具。埋藏在显微层面分子系统机制蓝图中的线索是这一目标的核心。这种分子系统机制,也就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样子。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对生命的理解源于代代相传的故事,起初是口耳相传,后来则是通过书面文字流传。然而,最近几十年,人们发现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深处的记录要比所有的书面记载更加有力,也更加深刻。
同源异形基因告诉每个细胞生长的时间和方式,与病毒RNA相遇所获得的ARC基因似乎是我们记忆能力形成的关键,我们的细胞和体内大量微生物群之间发生着遗传物质水平转移——凭借新近获得的破译生命基因密码的能力,我们更加理解人类的本质,也找到了与疾病之间长期斗争的新目标和方向。
但是,在人类大脑退化问题上,我们在基因解码方面迄今为止的成果还没能发挥什么作用。现在我们顶多能告诉患者,他们的X基因可能和Y疾病有关联。由于试验性实验缺乏足够的参与者,就目前而言,这个结论对医生和患者尚无用处。
我时常请几位认识的生物学家闭上眼睛,想象在人体37万亿之多的细胞中,其中的一个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我请他们带着我漫游细胞,给我讲述他们看到的画面,就像《神奇校车》中弗瑞丝女士引导班里学生那样。很快就能发现,这画面极不完整,其中很多部分我们都是靠着想象,自以为是地拼凑、填补。不过还好,我们当前进展讯速。
回想十年前,我才初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劲。在这十年之间,我们发现了嵌合现象、表观遗传学、转译后修饰、基因多效性、上位性和其它种种。这些发现逐渐揭开这一过去完全未知的领域的面纱,对我们共同对抗疾病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对150,000名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基因测序, 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会有什么关于个体疾病机制的新发现吗?会出现多少新的制药靶点呢?和所有对未知的探索之旅一样,这个研究的美妙之处正在于答案都是未知的。我们明白,仅仅依靠遗传学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实现终极目标,但是,它可以为新疗法奠定知识基础,与此同时,也让我们填补有关生命精微奥妙的知识空白,一探皮肤纹理间的乾坤。